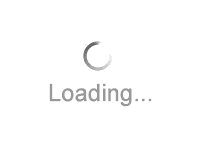- 热搜词
从《候场》中看三个李诞的分裂与互补~
小说《候场》以一个脱口秀演员自叙传的口吻,讨论了个人理想、职业精神、人生意义等不接地气的话题。它的作者是李诞,对,就是那个在《今晚80后》脱口秀大会中脱颖而出的李诞。
观众熟悉的作为脱口秀演员的李诞,在脱口秀节目中随和、轻松,带着温厚中的调皮、敏锐中的慵懒、叹息中的宽容,以绝无侵犯性的形象——既不帅得凛然,也不丑得奇特,在几分钟的碎片化时间里恰到好处地把握节奏,抛出他的“梗”,赢得一片笑声。
但在《候场》中,李诞却以一个思考者、怀疑者、焦虑者的形象,以近乎消极的体验积极地做出一系列人生追问。这使得《候场》不是一本故事书,而成为一本哲学书。
李诞:脱口秀演员·小说主人公·作者
镜头前的李诞有多轻松,《候场》中的李诞思考就有多沉重;镜头前的李诞多随意,《候场》中的李诞就有多严肃;镜头前的李诞多大众化,《候场》中的李诞就有多个体化。两相对比,我们看到一种分裂。而这种分裂,是第三个李诞——作者李诞的分裂。
虽然我们都知道,小说中那个叫李诞的主人公并不能等同于现实中那个脱口秀演员,但身份、经历的高相似度与二者形象的强烈反差,很容易让读者产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联想。尤其在《候场》中,作者李诞一再强调主人公李诞的诚实叙事态度,读者更是很难不将两个李诞进行勾连。当然,你也可以假设二者完全没有关系。可是即便如此,我们依然会看到两个李诞:一个是脱口秀现场活跃的说话人李诞,一个是独处时沉思的写作者李诞。在不同的语境中,他们判若两人。虽然《候场》中,作者李诞通过主人公李诞保持着他诙谐的口吻,但讨论的话题和思维路线迥异于节目里的他。
通过自己的主人公,作者李诞以思辨式的絮语,不断叩问“人为什么活着”这个终极性问题,用向往自由的天性抵抗被同化的危险,以保持幻想的权利和抽身的可能。他塑造的主人公李诞茫然、悲观、缺乏目标,总是处于精神漂浮状态。这个李诞与作者究竟有多大重合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位理性天空的悲伤飞翔者,显然至少是作者的部分代言人,而他所表达的疑问都与现实生活中那个脱口秀演员存在巨大的形象裂隙。
我们看到的《候场》主人公李诞,总是在不断自问:“我在忙什么呢?”“我究竟来这儿干嘛?”“这儿指代哪儿?”并且自答:“我根本不知道为什么干上了这个,正如我不能真的知道我为什么干了任何事,理性给出的理由都是后找的。”伴随这些“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我在干什么?”“我为什么干这个?”等本源性追问,主人公在专业、名利、交流、攀比等围困中突出重围,获得了置身事外的旁观视角。他冷静地看着这些无解的问题一律指向偏于颓废的终点,在富于悲剧意味的自省中走向理性的茫然。
如果说他与朋友、上司、老婆、英语老师等人的一番番对话很具生活实感,与死亡的对话则是跳脱现实的魔幻之笔。也许读者们都以为《候场》会以李诞的死作为结局,没想到作者笔锋一转,用秦典放达的不是劝慰的劝慰——“我也不劝你好好活着”“你真的帮助过很多人”“总归都会过去”拯救了这个濒死者,给读者一个温暖而又意外的结局。这个结局的设计,让主人公在黯淡的穷途末路绝处逢生,重新被理性之光照亮。
自嘲:充满同情的智性降维
没错,我们在《候场》中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李诞,不再是那个机智、幽默的公众人物,而是一个困顿的思想者。但是,他们依旧是同一个人,虽然在不同场域谈论不同话题,但他们对待世界的洒脱态度是一致的,并同样以自嘲的方式来进行自我呈现和表达。因此,在两相分裂中,他们又是相互补充的。作为一个有热度的脱口秀演员,李诞一句“人间不值得”圈粉无数,《候场》中再现了粉丝高呼这句话的场面。这句看起来消极甚至被误读为有“丧”文化内涵的“金句”,其实富含了不纠结、不在意的积极洒脱的人生态度。尤其当它与李诞自嘲的态度结合在一起,更成为一种真诚的劝谏,更为彻底地实现了解压之功效。
自嘲是一种不高看自己一眼,并对别人充满同情的智性降维。通过不断降维,李诞在脱口秀这种流行文化中脱颖而出。在洒脱的自嘲中,无论通过节目还是作品,李诞都在传达这样一种观念:普通人的生活、愿望其实很简单,我们没有必要相互欺骗。于是,他通过一个个段子、一个个“梗”,也通过《候场》,不断表达着:我也很庸俗,不行吗?我也很苦闷,跟大家没差别。这丝毫没有智性的光辉、神性的光芒。
不由让人想起上世纪80年代末期,王朔在《我和我的小说》中曾宣称:“我立意写小说,的确是想光明正大地发点小财。”他把写作称为技术活儿,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知识界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无论承认与否,王朔式黑色幽默曾经影响了一个时代的语体风格和文化趣味。除了王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还有一位叫周星驰的艺人对流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周星驰风格自由行走于雅俗交界地带,在自嘲和谐趣中生机勃勃。文化的积累与影响往往是无心栽柳,从某种意义上说,李诞的洒脱与自嘲可能是王朔态度和周星驰风格的延续。不同的是,李诞又向前走了一步,他以形而下态度讨论形而上问题。
如果愿意仔细品味,我们还可以从《候场》中看到王小波的影子,冷眼热肠中,谈吐是通俗的,心灵却是脱俗的。这种超越于物质表层的内心深处的渴望,虽然不甚明确,却将李诞从流行文化中标识出来,贴上了知识精英标签,不管他愿不愿意。因为这是脱口秀演员李诞、作者李诞、主人公李诞之间相互补充的结果。
小说:超越自我消费的“独处房间”
正因为既存在分裂又能够互补,《候场》中的主人公李诞就介于现实中脱口秀演员与写作者的中间状态:既以自嘲的方式降低自我期待,委婉地向现实妥协,与世界和解;又暗暗反抗着定制的生活,渴望“保留拔腿就走的幻想”,时有“忽如远行客”的恍惚。
事实上,自嘲是一种自我消费。所谓“吐槽”,既有一吐为快、不吐不快的淋漓,也必然有约束和限制下的吃力。因讽刺并非百无禁忌,趣味也不能脱离大众审美,李诞的脱口秀文化便形成了自我消费的定势。譬如消费童年记忆、父辈癖好、地方风情、上下级关系等,都围绕个人生活经历和趣点展开。李诞的脱口秀创作依托于这种自我消费,且很难超越这个框架,时日长久,难免不虚空乏力。无论富含多少智性成分,无论他怎样“用语言里的含沙量冲出一个平原”,脱口秀节目也不适合表达虚空乏力时的自我怀疑和意义追问。
于是,李诞以对于小说文体功能的发现——“小说将把真相不受控制地显现在虚构中”,来成全另一个自我。其实,孰为真实孰为虚构并不紧要,对李诞来说,小说仿佛一个独处的房间,一个不用在人前表演、不用设计一个个“梗”的房间。在这个房间里,可以换一种聊天方式,可以想象“众云死在天上散在天上,天上有墓。”在这个房间里,可以静静地想:我们以什么样的态度生活、存在?
小说让李诞获得了换一种角度审视世界、审视自我的自由,也让他拥有了用理性和诗性重新结构世界的创造力。读者则借《候场》延伸了观察李诞的目光,看到了《候场》内外更具复杂性和丰富性的三个李诞,以及这三个李诞提供的关于人和人生充满张力的疑问与想象。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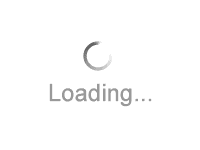 脱贫路上一个都不能少02-02
脱贫路上一个都不能少02-02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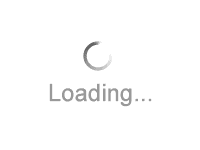 黑龙江新增22例确诊 9例无症状 现有无症状感染者531例~02-01
黑龙江新增22例确诊 9例无症状 现有无症状感染者531例~02-0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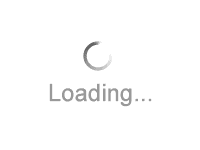 黑龙江齐齐哈尔10人网购涉疫奶枣,相关样本检测均为阴性01-31
黑龙江齐齐哈尔10人网购涉疫奶枣,相关样本检测均为阴性01-3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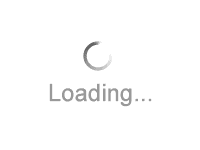 防控更扎实 运力有保障——春运首日探访武汉天01-28
防控更扎实 运力有保障——春运首日探访武汉天01-28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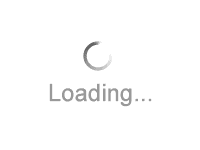 我国新冠肺炎疫苗接种已超2276万剂次~01-28
我国新冠肺炎疫苗接种已超2276万剂次~01-28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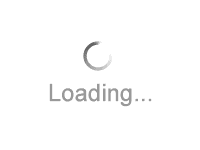 醉美山河,就在《中国新疆之历史印记》01-30
醉美山河,就在《中国新疆之历史印记》01-30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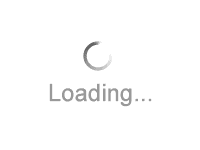 美国正将世界拖入流动性陷阱~01-29
美国正将世界拖入流动性陷阱~01-29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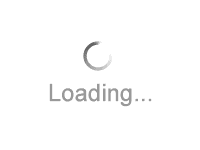 蔡奇主持北京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02-02
蔡奇主持北京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02-02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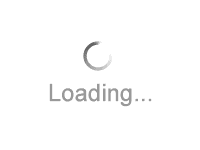 《云顶之弈》11.2版本狗头怎么出装 一起来了解下01-27
《云顶之弈》11.2版本狗头怎么出装 一起来了解下01-27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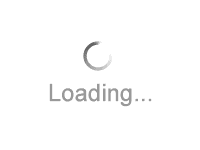 一品转债370723申购打新投资价值分析 一品转债评01-28
一品转债370723申购打新投资价值分析 一品转债评01-28